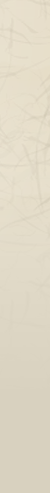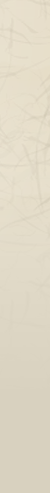2016年2月末,有幸随学校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和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前往日本,就图书馆、纸张、古籍保护与修复等主题进行一系列的访问和学习。这11名学生就是复旦大学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于2015年开始合作培养的全国首批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
一共是七天的行程,先后拜访了奈良县立图书情报馆、福西和纸本铺、片冈古民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神保町古书店街、静嘉堂文库、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国立公文图书馆(内阁文库)、东京小津和纸等12处机构。
奈良县立图书情报馆是到日本的第一站,该馆建立于2009年,建筑风格现代简洁,周边大道上栽满了樱花树。据接待我们的松村顺子小姐介绍,图书馆的主旨是“面向未来的服务”,因此采用了先进的全自动书库系统。我们有幸进入书库参观,体验了现代化的便利与神奇。全自动的运输轨道就像运输的巷道,分成横向和纵向。所有的书籍根据尺寸大小安放在定制的书箱中。每一本书入库都会有一个编号,由计算机软件系统记录书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书被提取借阅之后,哪些书箱又产生了新的空间,以便后续的自动化操作、填充还入书籍。因此在这一全自动系统中,书只需要一个代码,用于计算机的识别,不再涉及学科分类或语言、地域等。一个代码即该书的唯一身份,可供随时随地调阅。图书馆在三个楼层设立了书站,是一个自动出书的窗口,图书馆员扫描好书的代码,等上两三分钟,书就会自动运出。
科技带来的快速高效让我们这些文科生产生了一些思索。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可能知识的提取是定向的,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确定书目,这些都是自动化书库和检索系统可以满足的。然而,开架书库中学科分类安放图书的好处,还在于能让学习某一领域知识的人搞清楚学科演变的历史,因为同一主题的书都被陈列在了一起。就我个人而言,喜欢泡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一大乐趣还在于可以徜徉在书架之间,于不经意时邂逅一些新知和新喜。
所有图书馆都面临空间不足的难题,采用全封闭自动化书库是解决的方法之一。目前奈良县立图书情报馆的藏书量可以达到100万册,节省下的空间用于编辑室、演出室、甚至地方土特产售卖等服务于奈良当地人民的公共设施。在图书馆的一层,我们还看到了抢救室。
离开时已是黄昏时分,我们看到不断有市民前来借阅图书。日本国民的图书阅读量是世界第一的,阅读环境也是令人羡慕的。
第二天的一大早,我们就向奈良吉野山进发,去探索日本和纸传承之家,福西和纸本铺。日本有四大和纸,分别为吉野纸(奈良县)、土佐纸(高知县)、越前纸(福井县)、美浓纸(岐阜县)。我们去的吉野山内有好几家制作和纸的人家,都位于山的深部,一路开进,道路上的气温提示从6度降到了0度。造纸是一项“天时地利人和”的工程。吉野山种植的楮树、宇陀川清澈的溪水、代代相传的世家、以及寒冬时节的温度。据福西主人介绍,每年的冬天是做和纸的好时节,因为够冷。他现在每个星期的产量在800张左右,大部分的订单来自国外的知名博物馆以及个人收藏家。福西家的造纸技术传到他手里已经是第六代。他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子相传”的匾幅。日本工匠的代代相传也面临式微。这样的传承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荣誉感。除了和纸手漉(中文为“手抄”)技人的技术,还需要其他工匠的配合。福西家漉纸用的簾桁,由名家制作,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这样的工匠全日本只有1-2人。他们用的楮树,种在自家的后山坡上,树龄从5-40年不等,必须悉心照顾。每年的光照、降水不同,最后出品的和纸光泽色度都会有差异。晒纸用的大木板是江户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刷纸用的马鬃刷也很有讲究,第一遍硬、第二遍极软,如不是出自名工匠之手,那种不可言传的感觉拿捏无法恰到好处。
福西家的和纸制作,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手工操作。煮纸浆、挑纤维、漉纸、成型、晒纸。每做七张和纸要人工搅拌一下纸浆,每做七十张之后添加原料,然后再搅拌,这道工序是福西和纸唯一用到机器的地方。最关键的是漉纸,使用的工具是底部镶有竹帘的横木架,即“簾桁”。工匠平持簾桁,用它在滤缸里掬取纸浆,同时前后左右地晃动,使竹帘均匀的粘上纸浆。这也是制作和纸中最关键最难的步骤。流滤的要领是“不断的重复摇曳”。纸浆的水波一次次的晕染开,犹如沙盘里的纹路肌理。水流从竹筛滑落,留下半透明的和纸原浆。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每一位在场的老师和学生都在福西先生手把手的帮助下试做了一张。
好的匠人需要毅力,日文为“根性”,福西家的墙上挂了很多这一字符,相信是用来鼓励自己的。好的匠人也需要自信,这样才能有自豪感。好的匠人也需要较高的悟性和审美情趣、于细节处的不厌其烦、繁华世界里的甘于平静。在纷繁的现代社会,能抵得住诱惑、静得下心来,在大山深处造纸是极不容易的。
福西家的和纸根据质量和品种不同,每张的售价在300-800日元之间,囿于温度季节,产量并不会很高,收入也不会很多。而在制造之前的准备,却是贯穿于整年之中的。这一份艰辛和坚持,只有在参观过整个和纸制造之后才能体会。手漉和纸已经在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福西家里陈列最多的除了各种奖状之外,就是福西家每一代人从事手漉和纸时的写真。他表示他们家制造的和纸可以保存几千年。在我们结束访问,回到复旦后。就收到了福西先生寄来的信件,他表示日本圣德太子遣隋使从中国习得造纸技术,回来教会了吉野的住民。一千三百年来,这门技艺还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作为对中国的感恩,如果有什么需要他做的,请尽管告诉他。
下午我们访问了同样位于吉野山的片冈古民家。主人片冈老先生已经年逾90岁,得知复旦大学的学生要来,特地亲自出来。片冈家的住宅建于宽文10年(1670年),已经纳入日本国的重要文化财。古屋门口种着树龄800年的神木,家里用的灶头是明治时期的,我们去的前一天还生过火。屋子的顶盖用麦秸秆厚厚地铺成,每过2年就要请村里的工匠来重新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麦秸秆的屋顶一方面比较轻,一方面中间有孔,便于排水。我们去时恰逢初春,麦秆周边开出了红色的小花,与老人家庭院里的梅花相映成趣,一片生机盎然。在日本的神社,也有这样的传统,每过20年要换一次屋顶,叫做“式年造替”,“式”在日文里就是二十的意思。位于奈良的春日大社去年3月27日将神迁出、开工换屋顶,完工将在今年的11月6日,再把神请回正殿。
片冈家在村里威望极高,从他的祖祖辈辈开始就负责保存村里各个人家的账本,已经延续了300多年。村里发生纠纷,也会到他们家来协商,因此片冈家收藏的文献里还有一部分是类似于“诉状”的文书。
片冈老人从年轻时就跟着祖父一起整理家里收藏的文书,对所藏的资料进行编目,还自学修复和装帧。他的家就像一个博物馆,客厅里摆着源氏物语的屏风。他收藏有200多种古典汉籍,目前正送往东京检定。老人还拿出一大盒中国的湖笔、徽墨,制作精美,图案吉祥,或鎏金或染青石色,让人惊叹不已。
在他家所有的宝贝中,最让我们爱不释手的是一本在佛教徒中间使用的并非佛经却类似于信佛之人谈修炼心得的书。据说当时大户人家才有,片冈家的保存十分完好,老人也视之为传家宝。书所用的纸张十分紧实,造纸时掺入了云母,因此可以看到类似珍珠般的光泽。我检索相关资料发现,添加天然矿物云母之后,在自然的光线下可以呈现出柔和的闪亮,是种高级的纸张。该书成书在明应七年(1498年),是在日本室町时代的后期,该年日本京都附近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
对于古籍保护来说,空间是十分重要的。片冈家的文书大致存放良好,除了虫蛀和火烧造成的一些损害,纸张的酸化等都不太严重。当天接待我们的除了片冈老人,还有他的儿媳妇。希望老人长寿健康,明年带第二批学生去的时候还能继续和他交流。
第三天的行程安排在京都。上午我们如约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情报学研究中心。中心的建筑物是西班牙罗马式修道院风格的,建于80年前,这栋白色的建筑是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的标志。据说当时所在的1930年代,日本受到美国境内西班牙风格流行的影响。原京大校长、时任文学部教授的滨田耕作提出,“我不认为为了研究中国,就一定需要建造雕龙画凤、卷棚攒尖式的屋顶”。后由设计师武田五一承担了设计,采用西班牙风格,成为日本近代建筑的杰作。中心书库内藏有30万册汉籍。十分遗憾的是,书库内部正在修整,学生们没能入库参观。去年樱花时节,我曾和复旦老师造访书库,当时受到热情接待,进入书库近距离接触。书库位于尖塔内部,是全通的挑空设计,2-3层为铁骨三层构造的书库,三层以上是全玻璃的天窗,用于自然采光。书库1层可以同时作为阅览室供研究人员使用,地下一层为密集书库。挑空设计使自然通风变得极其良好,再配合利用空调和除湿机略进行温度和湿度的调节。
研究中心的永田教授和梶浦教授与学生进行了座谈,介绍了研究中心的“全国汉籍数据库”以及他们在古籍保护、利用和修复上的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收藏中国古籍,主要是用于研究,所以只要研究人员有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开放让其使用。对于有破损、需要修复维护的图书,研究中心会请日本专门的修复公司或匠人来处理,事前订立协议,进行对接,将相关要求和最终效果商谈好。研究中心建筑的内部没有专门的修复室,所有修复都委托他人进行。目前也受到经费限制等原因,面临一定的困难。琉璃厂的陈济川等人80年前就赴日本,在京都大学修复古籍,我们也期待这批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日后能有机会赴海外修复古籍。
饭后大家还前往著名的“吉田竂”外围参观,为了尊重住在其中学生的隐私,我们并没有进入宿舍内部。对于现在住在窗明几净、设施齐全的复旦研究生宿舍的学生来说,也许很难理解为何如此破旧的、100多年前的大正时代的和式宿舍是一种荣誉。从吉田竂里走出的都是日本的精英。在他们心中,传统的就是正统的。住宿费为一个月2500日元(包括1600日元的水电费),合人民币不到150元。吉田竂实施自治管理,通过全体住宿人员的合意(并非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各项大小事宜,比如添置设备、新进人员等。吉田竂里的学生男女各半,宿舍旁堆着破旧的自行车、养着鸡鸭(都是届时用来煮食的)。房间为和式,极其狭小。住进吉田竂是一种磨练,也意味着进入了某个圈子。
京大的周边的美景让人留恋往返,我们还是要赶往下一个学习交流的地方,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该馆相当于档案馆,于1963年建成,它的宗旨是京都地区相关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展示。其所藏的《东寺百合文书》是国宝,在去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记忆遗产”。我们到访时正在进行特展,馆员告诉我们其全文已经数据化,可在他们的主页上浏览。《东寺百合文书》记录有日本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寺内的运营状况和法事等内容,约2.5万封文书,展现了当时的生活风貌和文化。
文献科资料主任松田女士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书库,其中收藏的地方资料和专题资料之全让人感叹。在书架上,出于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敏感,我看到了很多令人兴趣盎然的题目。比如《台湾虫害调查报告》、《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工业部报告》、《台湾震灾志》、《台湾茶叶传习所概要》。另有一组关于朝鲜的报告,分别包括灾害、鬼神、小作惯习、市场经济、生活状态、风水、巫术、外国人眼中的朝鲜等。所有都是成系列印刷保存的,充分体现了日本对殖民地的研究之细致、周全。还发现了14卷本的青森苹果发达史、每年成册的神户港港口情报等,真是随便哪个都能做成有趣的课题。书库里保存了大量的日本报纸,1966年之前的都会进行纸板的保存,虽然已经有大量做成了缩微胶卷,他们还是坚持在空间紧张的今天,留出一大部分存放实体报纸。
最令人兴奋的是回到专门的贵重资料阅览室,展示我们请求的资料。其中一大组展现生活风貌、当时贵族文化消费的书吸引了我们。一副立体的京都皇宫图记录了建筑原来风貌,包括门所在的方向,花瓶摆放的位置等。要预约看京都御所是极难的,通过这张图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还有一个卷轴《类聚杂要抄》,“御齿固”的部分。画的是平安时代正月头三天,天皇在清凉殿举行供奉御药的仪式。所谓“齿固”,是牙齿坚固,延长寿命的意思。画师呈现出来的食品包括:萝卜一杯、茭白串两杯、押鲇(腌渍的香鱼)一杯、盐煮香鱼一杯、野猪肉一杯、鹿肉一杯共七杯于食盘之上,再加上镜饼。这些食物都是有一定硬度,可以用来锻炼牙齿的。松田女士告诉我们,这么多的食物天皇只是用筷子碰一下,就表示都吃过了,以完成仪式。
文献室的若林先生拿来了刻本的《汉书》,让复旦的老师帮忙确认所在年代是否和他们鉴定的万历末期相符,双方相谈甚欢。我们提出想看一下木活字,他们也欣然应允,拿出了该馆收藏的600年前的一套。并推荐我们去京都的圆光寺参观,寺内保存有日本最古老的活字印刷5万个。除此之外,还看到了日本和服纹样、和纸的样本集、当时大名手抄的俳句集。一些书的封皮是专门从中国进口的织物,即使年代久远,精美仍不退色。
此次赴日考察的学生均是古籍修复专业的,因此我们也谈起了修复。若林先生告诉我们,在日本除了修复师之外,还有更高级别的国宝修理装潢师,对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等美术工艺品进行修理。主要是针对在日本、亚洲等地制作的绘画、典籍、古文书、历史资料等。他们还有自己的联盟,简称ACNT(the Associat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ional Treasures),每年定期举行研讨会和研究会。目前修复技术高的工匠都在博物馆,最好的可能在皇宫。
东京的第一站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我们得到了大木康教授的热情接待。大木康教授的研究专长是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这样一位权威而热心的学者,近年来一直和复旦大学的文史专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我们的学生也有幸能聆听他亲自用中文讲解。研究所藏有汉籍17多万册,其中大部分是珍本和善本,开放供学者研究。
到达东京的第二天,行程也是充实而忙碌的。上午我们前往静嘉堂文库参观访学。创始人岩崎弥之助是三菱集团第二代社长,从明治25年(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郎扩充了藏书。湖州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都在1907年由其子陆树藩售于岩崎小弥太郎,运往日本后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文库现在的藏书量为20万册,其中汉籍12万册、日本古籍8万册。
静嘉堂文库位于日本东京都高级住宅区世田谷区武藏野一带的一座小山上,沿着小山径往上走,两侧是丸子川和谷户川两条活水。据说天气好的时候在山上可以远眺富士山。静嘉堂文库有图书馆和美术馆两栋主要建筑,还有一个美丽的庭园和岩崎弥之助的墓冢(西式墓室的铁门上刻着“二十四孝”图案)。由于图书馆的接待室十分小,我们一行15人需要分两批进入。接待我们的研究员成泽女士已经在前期的联络中非常清楚我们来访的意图,也准备了大家想要看的古籍。由于静嘉堂文库不接受初访者以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申请,我们在前期联络的时候由专人专程拜访,才保证了这次行程的畅通无阻。
据成泽女士介绍,岩崎家的后人和陆心源家的后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都有互访。她是第一次知道和接待像我们这样研习古籍修复的专业学生。我所在的这一组,调看了《李太白文集》。目前存世的《李太白文集》宋版仅存两部,一部就在静嘉堂。该书本卷《草堂集序》第一页有藏书印章十几枚,其中可以辨认的有王杲、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王文琛、钱应庚、蔡廷桢等名家,十分珍贵。书籍的保存情况非常好,主要得益于陆心源时期和历代收藏名家的精心呵护。成泽女士告诉我们,从皕宋楼购入的书籍都没有修复或特别的维护过。
下午我们前往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继续学术访问。小林研究员和高木研究员带领我们参观了书库,并陈列了早大所收藏的汉籍,也包括高丽(朝鲜)的活字印刷本佛经、长崎的木刻版画、幕府将军的家书等供学生们查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东亚的文化交流情况。早大的中国古籍藏书量非常大,局限于空间问题,书摆放得十分紧密,纸张的酸化程度也较为严重。小林先生告诉我们,早大会对破损的古籍做一些修复,其原则是所使用的材料都能使修复的痕迹消除,并随时可返回书破损时的原貌。日本图书馆的通常做法还是将书籍修复委托给专门的公司,有技术工匠来进行专业的修复。
我们这次去的学校,遇到了很多复旦的有缘人。早大图书馆的高木先生1994年期间到复旦留学,师从古籍部的吴格老师。高木先生特意带来了他留学时期的笔记和日记,供各位同学分享。笔记里有吴格老师写给他的讲义要点、介绍他去北京、江苏等地访学的介绍信;日记里有高木先生和同学的书信往来、生活开销记录、日程安排、还有他眼中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等等,留学生活跃然纸上,读来趣味盎然,也让我们这些复旦人甚为感动。这几大本的记录既是高木先生留学生活的财富,也是复旦和早大之间亲密关系的佐证。
在日第六天的上午,我们前往我曾经留学的庆应义塾大学。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拜访位于旧图书馆内的斯道文库。文库的藏书量约为七万册,贵重汉籍都配有桐木盒子,外围也用网兜固定,以免地震时倾倒。根据捐赠人的名字,分别设立了椎本文库、安井文库、浜野文库、龟井家学文库、平岡文库、大曾根文库、今关文库等特殊文库。还有一部分根据寄存资料设立的文库,我们看的主要就是其中的“坦堂文库”。
为我们开讲的高桥智教授是汉籍版本学者,他也曾在复旦留学,1986年至1988年在复旦古籍整理研究所进修,导师为顾廷龙、章培恒教授。去年被我校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为研究员。高桥智教授的一口中文受当时周边江浙同学的影响,有了吴语化的特征。他绝对是一个“中国迷”,在他的心里,中国的都是最好的。他拿给我们看的一套《汉书》,经过日本匠人为时七年的精心修复,金镶玉的装帧,还特地配上了丝质的函套,让人叹为观止。高桥先生说,丝质的函套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工匠做的,但他认为还是不如中国工匠的手艺好,函套的硬度不够、自由翻转的程度也不够。
接下来的一站是位于皇宫近侧的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它属于日本中央级的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阅览利用和展示从国家各行政机关接受来的历史档案,同时也为谋求档案的有效利用而开展调查研究。文库的藏书总量为54万册,其中日文书31万多册、汉籍18万多册、西文书4.5万多册。 一些书籍如宋版《庐山记》等书被指定为重点保护文物。
除了书库,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书的修复。这一路走来,各个研究机构都告诉我们,内阁文库在修复方面是做的相当好的。业务科修复系长阿久津智广是一位36岁的年轻人,他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研习修复10多年,对于和纸的研究也颇为精道。他们也面临着修复人员短缺的现实。目前每年的修复数量在7000册左右,其中大约300册是需要重度修复的。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书籍修复的重要性,公文书馆在2楼设立了专门的修复室,半透明开放,供来访者了解修复的一般情况。若干年前,他们就引入了极薄和纸(0.02mm),使用以楮为原料的和纸作为修复纸。现在每年还接受海外研修生来馆内学习修复技术,并帮助受到地震、海啸等影响国家的档案和文书修复。
在国立公文书馆终于看到了神奇的“叶铸”(leafcasting)机器(日本将他们国家制造的这一类机器称为“漉嵌机”,复旦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也有一台,我们暂且称之为“纸浆补书机”),也解答了我们在庆应斯道文库看到的那套修复精美的《汉书》是如何做到如此高程度的修复的。所谓“叶铸”工艺是指利用纸浆修补残缺和虫蛀的部分,在叶铸器的帮助下,可以精确测量替换缺失部分所需的纸浆的多少,将纸浆的厚度与纤度和原件比对,当纸浆调制完成后,通过吸力作用将纸浆淤积以填补文件的缺失部分,多余的纸浆则被排出,原文件以及新修补好的纸质文献要在一定压力下晾干。这样的技术可以始终如一地将新的纸质纤维精确地粘接到已损坏的纸制文件上。现代高科技的应用,帮助纸张修复实现了神来之笔。
我们赶往行程最后一站是位于日本桥的和纸专门店—小津和纸。小津和纸创办于江户时代的1653年,是小津家族产业的一环。在3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开拓、繁荣、经济危机时期的调整。从曾经涉猎金融、纺织、百货、对外贸易到最后回归于专业造纸的初心。小津集团现在只剩下位于日本桥的这一栋大楼,一层是和纸商店,一旁有体验“手漉和纸”的教室,三楼是小津史料馆和艺术馆,定期开展各种有关和纸的展览,其他为办公室。我们去的时候艺术馆正在展出日本各地制造的和纸,奈良吉野山福西家的宇陀纸赫然在目。史料馆用各种缩小版的道具情景再现日本和纸制作工艺的各个步骤,还有很多用和纸完成的人偶和装饰物。“人制造了纸、纸制造了文化”是小津和纸要传递给我们的理念。
和纸的美在于纸张超强的韧性(使用楮、雁皮、三桠的纤维为原料)、超长的保存时间(千年以上)、以及较小的产量(原料限制和人工生产无法实现大批量。现代科技的纸张可以在鲜艳、光泽度和缤纷的图案上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当我们摸着朴实的和纸、似乎在和大自然以及将它制造出来的工匠对话,那一份精神愉悦和情感传递是难以比拟的。
在这次的日本之旅中,我也产生了这样的共鸣或者说是错觉。短短的七天,从纸张、活字印刷、制书到图书馆、古籍修复,回望人类探索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先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美的坚持以及无限的创造力。
在这个喜欢追问“为什么”的时代,也许很多人会对“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意义刨根问题。这也是我刚接触从事这一事业的个体时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传承的一部分,一切文化遗产都是面向未来的。一路遇到的工匠、学者、相关从业者,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对自己的专业近乎于痴迷的热爱。我相信,也许就在寻找修复办法的路途中,我们逐渐还原出先祖探求世界的模样;重温他们的技术、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也在修复和还原人类这一生存群体的历史。
(作者:金莹 本文精华版发表于《书城》2016年第五期)